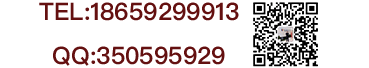以案说法◇犯罪所得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案 情
程某与肖某于2010年3月8日登记结婚。2013年12月至2015年2月,程某通过签订多份月利率2%借款合同的方式共诈骗周某某676万元。2013年12月11日至2014年11月29日,程某57次向肖某建行卡共转款380余万元。2014年1月16日至9月25日,为购买汽车、住房并装修商铺,肖某7次用建行卡共支付206万余元。2015年3月9日,程某与肖某经法院调解离婚,肖某从婚姻共同财产分配中取得了前述汽车及住房所有权,以及商铺中原由夫妻共同享有的份额。2017年9月,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程某诈骗周某某676万元后转入肖某等人账户或用于个人消费,判处程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15万元,责令程某退赔周某某676万元。但程某一直未予退赔。 分 歧 针对程某合同诈骗周某某款项后转入其妻肖某账户的380多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评 析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
2018年5月,周某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肖某在380余万元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肖某在其建行卡转入款范围内与程某成立夫妻共同债务,判决支持周某某诉请。
肖某不服一审判决,以程某在从事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属于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程某的涉案债务虽然属于超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但周某某已举证证明其中的380余万元转入了肖某账户,本案在该款项范围内成立夫妻共同债务。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第一种观点认为,程某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380多万元属于其诈骗犯罪所得,生效刑事判决已作出追缴或退赔全部676万元诈骗款项,周某某应通过刑事判决的执行程序实现权利救济。因肖某与诈骗犯罪活动无关,且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全部诈骗款项都属于程某的个人债务,周某某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不能成立,肖某不应承担清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基础债务关系是共同债务成立的前提。追缴退赔虽然属于刑事责任,本质上则具有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属性。显然肖某不具备成立共同侵权之债的条件。而从合同角度看,尽管程某已被认定为诈骗犯罪,但并不影响其与周某某的借款合同效力。合同之债是本案的基础债务关系。虽然涉案380多万元款项属于程某诈骗犯罪所得,但肖某只将其中的206万多元用于购买家庭房屋、汽车及商铺装修,故仅该部分已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第三种观点认为,同意第二种观点对206万多元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虽然从文义解释看只限于夫妻共同生活范围,但实质则是非举债方分享了另一方负债所带来的利益。利益分享的方式不仅包括夫妻共同生活与消费,也包括非举债方基于个人意志对债务利益的任何支配或处分。借助法律的扩张解释,本案可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8年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380多万元的夫妻共同债务成立。
一、追缴退赔是刑事责任保障制度下特定的民事责任承担
在侵财性犯罪中,受害人财产权利的救济途径通常有两种: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侵犯或财物被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受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因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缴或责令退赔。《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应只限于第一种,第二种情形只能通过追缴或责令退赔处理。法释【2000】47号第五条曾规定: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但现行刑诉法司法解释施行后,该解释已于2015年1月废止。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着问题的批复》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依法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被告人返还被占有、处置的财产,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批复的精神看,“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将造成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的重复、冲突。”因此,批复视追缴退赔为刑事责任制度下特定的民事责任承担,不言自明。
追缴退赔因犯罪行为而生。犯罪行为属于广义上的侵权行为,与民事侵权有相同之处:无法律或合同依据而非法获财,具有违法性;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行为与损害事实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民法通则第117条规定,侵占国家、集体或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追缴退赔虽属刑事责任,但其符合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中的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特征,本质上具有侵权之债的法律属性。是刑事法律规定由司法机关直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依职权而非由受害人申请启动的侵权民事责任追究措施。但从实务层面看,由于追缴退赔自身的局限性及缺乏细化规定,即使本案涉案赃款去向清楚,司法机关对肖某名下除现金之外的其他资产如房屋的强制执行也持否定立场。制度的弱化迫使受害人转入民事诉讼途径。
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适用
本案程某的诈骗手段是与周某某签订月利率2%的借款合同。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已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因此,即使程某的借款行为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因周某某未以受害人身份行使撤销权,案涉合同仍然有效。尽管现行立法基于国情和刑事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排除了受害人对刑事被告人的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民事诉讼途径,但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刑事制裁性不能消灭程某与周某某间的合同法律关系,与双方间的侵权之债一样,合同之债也属于本案的基础债务关系。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其中的“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是指所举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由此来看,转入肖某账户中的206万多元因已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本案在程某与周某某间的借款合同之债基础上,肖某就该部分款项成立夫妻共同债务没有疑议。笔者认为,170多万元余款性质的认定,需要借助法律的扩张解释来理解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从本条的立法意旨分析,一方举债而非举债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法理基础,是所举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非举债方在共同生活中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成立夫妻共同债务的落脚点在于非举债方对债务利益的分享,夫妻共同生活只是利益的分享平台、立法界分夫妻共同债务的载体。根据举轻明重的法理,若所举债务的利益由非举债方个人独享,其与举债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就更合乎情理,具有正当性。因此,即便肖某独享了170多万元的债务利益,由其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显然也符合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立法本意。该情形尽管不为本条的文义范围所涵盖,借助扩张解释方法仍可适用本条规定,认定170多万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认定
2018年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程某诈骗行为形成的侵权或合同之债显然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范围,应当认定为其个人债务。但从前文分析来看,周某某举证的银行转账明细足以证明肖某分享了380多万元的债务利益,符合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立法本意,应当认定该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进而适用2018年解释第三条的但书规定,认定本案在该款项范围内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需要说明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本案将程某诈骗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在380多万元范围内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支持第三人周某某的权利主张显然与该款存在冲突。其涉及本条与2018年解释第三条的关系问题。上述第二十四条饱受公众与法律界质疑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家事代理中的“共债推定”无任何限制地推及到婚内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加之几种除外情形这一“名义上属于‘可推翻的推定’,但实际上已接近于‘不可推翻的推定’或‘法律拟制’”,导致大量无辜的非举债方“被负债”,背离了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立法精神,在司法实务中近乎以“婚内标准”取代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共同生活标准”。而2018年解释以家事代理制度为基础,运用“共债共签”、家事代理范围内的“共债推定”,及超范围时的债权人举证责任负担三个法条,来构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其较之第二十四条更具科学性和正当性。因此,根据新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本案应当适用 2018年解释第三条。